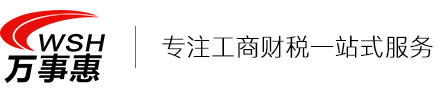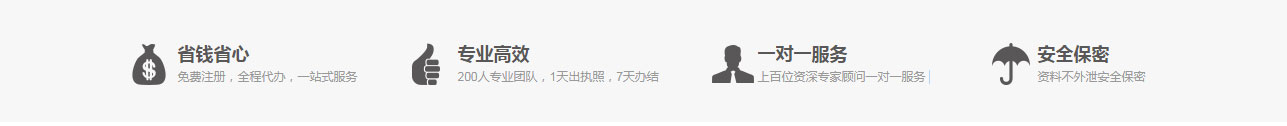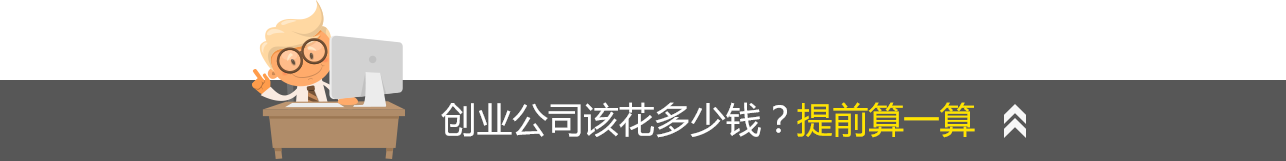商标权救济与符号圈地
2021-02-07 15:17:34
上标——中国商标交易的领先品牌;商标转让,专注于商标转让注册平台14年,商标注册转让金额在全国遥遥领先,商标注册,商标费用,商标注册时间_商标转让流程,商标买卖,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嘉兴/温州,热线:document . write(is phone);
【摘要】商标的形式是符号,但只有被称为市场信誉的符号才是商标。商标法的目的是保护市场信誉,而不是虚拟空的符号。中国存在严重的符号圈地现象。所谓“符号圈地”,即以商标权的名义,实行符号垄断。主要有两种表现:1。注册中的符号圈地;2.权利行使中的象征性圈地。中国商标救济制度的四大缺陷是纵容象征性圈地的制度根源:1 .过分迷信商标注册的效力;2.过度漠视商标使用的有效性;3.符号价值的错误估计;4.“商标使用”和“符号使用”的混淆。只有重塑商标权的救济制度,才能真正遏制符号圈地。[关键词]商标符号外壳浮雕
[郑文]
一、商标和符号
根据知识产权法理论,知识产权是知识成果权和商业标志权的总和。这种带有列举痕迹的定义留下了一个逻辑问题:为什么要将这两种权利合二为一,命名为“知识产权”?商业标记和智力成果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受法律保护,没有任何智力要求(如独创性或创造性),其价值并不来源于自身智力。换句话说,为什么一个非智力成果和一个智力成果在同一个辖区趋同?答案在于商标和智力成果都是符号。对于财产制度来说,最有价值的因素是财产的形式。相似的性质形式导致相似的使用性质的行为,相似的行为可以适用于相似的规范[1]。由于智力成果和商标在形式上是相似的,支配智力成果和商标的行为可以适用于相似的规范,这些规范组装成统一的知识产权法。
人类的智力成果在形式上表现为符号,符号是人工创造的具有参照功能的信号。所谓人类创造,就是在自然世界之外构建符号世界的行为。正如卡西尔所说:“在语言、宗教、艺术和科学中,人类所能做的就是构建自己的宇宙——一个符号化的宇宙,使人类的经验能够被他理解和解释、联系和组织、整合和概括。...人类的知识就其本质而言是符号知识。”[2]显然,商标既是标志,也是符号。常见的符号形式是商标和知识成果属于知识产权客体的逻辑依据。商标的构成要素,无论是文字、颜色、线条、声音还是作品,在形式上都表现为“符号的外观”。
但商标和智力成果看似不同,各自发挥着不同的符号功能。符号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指称功能。这个意义上的符号等于符号,符号的存在是为了代表另一个东西。这就是符号的初始作用。例如,“小桥”指的是交通设施。二是创造功能,符号可以组合构建新的形态,比如“粉色记忆”,并不是指任何事实状态。商标不是一个一般的符号,而是一个始终起着参照作用的符号。它的价值总是来自于所指对象的来源——商品或服务。因此,商标的符号形式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智力成果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符号形式,不再服务于任何参照物,就像苏珊?兰格说,艺术符号是“一种有些特殊的符号,因为它具有符号的某些功能,但它并不具有符号的所有功能,特别是它不能作为一种纯粹的符号来代替另一种东西,它也可以与存在于自身之外的其他东西相联系”[3。智力成果的符号获得了独立,而商标的符号永远不可能独立,一旦独立于商业信誉,就毫无价值。
综上所述,商标的“形”是一种符号,商标的“神”是隐藏在符号背后的商业信誉。如果一个符号不作为商品或服务原产地的代表而存在,它就不是商标。
二、符号圈地现象
所谓符号圈地现象,就是以商标权的名义进行符号垄断的行为。这是近年来中国日益增长的现象。符号圈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利用商标权取得的注册制度,将一个符号注册为“商标”,但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然后凭借符号垄断向他人主张“权利”,可以称之为“注册中的符号圈地”。例如,在全国蓬勃发展的“商标超市”中出售的商标大多是注册销售的虚拟空符号,从未真正与商品或服务相结合。第二,商标所有人将商标权的范围扩大到“符号权”。只要他人使用与自己商标相同的符号,无论使用是否属于商标意义,都主张他人“侵权”。这种类型可以称为“行使权利的象征性圈地”。比如,Xoceco电子公司在电视机上注册了“chdtv”商标,“hdtv”是“高清电视”的英文缩写,长虹电器公司在电视机包装盒上标注“hdtv ready”,Xoceco公司起诉侵权。显然,长虹公司用符号“高清电视”取其本义——高清电视。此时的符号“hdtv”并不是Xoceco口碑的身双,所以不是商标。Xoceco主张所谓的权利,理由是“hdtv”符号的形状与其商标“chdtv”的形状相似。事实上,Xoceco扩大了商标权,垄断了“hdtv”符号。
目前越来越多的象征性圈地行为结合了以上两种类型的特点,即选择商业活动中常用的一种符号作为商标进行注册,注册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以“商标权”的名义阻碍他人正常使用。这种行为具有以上两种类型的特点:1。注册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所以符号从未获得商标的本质;2.阻碍他人使用简单符号,他人的行为不构成商标使用,“商标权”人也无理主张“权利”。因此,既有注册圈地,也有行使权利圈地。
无论什么样的象征性圈地行为,都扭曲了商标制度的功能。社会付出巨大的立法、司法、执法成本,不是为了保护纯粹的符号,而是为了保护商业信誉。符号圈地现象的兴起导致一些企业不致力于建立市场声誉,而是在符号选择上投机取巧。一方面是圈地人的微利(唯一的成本是商标注册费),另一方面是诚实用户的清白。就像英国圈地运动时期的“羊吃人”现象一样,“符号吃企业”的恶果也是在符号圈地下出现的。追求利益是人的共性。以象征性圈地的手段谋取利益成为“中国的奇怪现状”,必然有其独特的制度土壤。法律界每个人都有完善制度的义务。讽刺人性的弱点是远远不够的。要把制度完善到“移位”。
诚然,立法缺陷和认知障碍是符号圈地现象的两大根源。所谓立法缺陷,是指我国过于宽松的注册主义,注册人无需实际使用商标或者证明自己有实际使用商标的意图就可以申请注册,所以将符号括起来是非常容易且廉价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抢注缺乏灵活的禁止条款,仅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已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目前,一些专业的符号圈地业主争相在小城镇注册小而著名的未注册商标,受害者很难证明自己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些注册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例如注册人与实际使用人有特殊联系,注册人知道他人先使用过),但可能不符合“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条件。另外,《商标法》没有规定在先使用权,使得符号圈地人与诚实用户之间的较量往往以圈地人的胜利而告终。因此,立法缺陷是“注册中的符号圈地”的重要制度根源。
认知障碍是“权利行使中的象征性圈地”的重要来源。如前所述,商标的形式是符号,商标与纯符号的关系只能借助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来把握。人们在感情中很容易将符号与商标混淆,商标所有人看到一个符号与自己的商标相似,就会误认为别人使用了自己的商标。非专业人士很难区分什么是“商标使用”。虽然不乏权利的有意扩张,但认知障碍是导致“权利行使中的符号圈地”的重要原因。
然而,立法和认知并不是本文的重点。立法的修改不是一天的工作,认识的进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本文的思路是:如何通过完善商标权的救济制度来遏制符号圈地现象。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不把“商标保护”误认为“符号保护”,就会让符号圈地人意识到自己的圈地是无利可图的,就会降低他们的圈地热情。因此,通过完善商标权的救济制度,一方面可以弥补立法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商标所有人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范围,这是治理符号圈地最接近的方式。
三、商标权救济制度的误区:鼓励象征性圈地
(一)过分迷信商标注册的效力
商标权是民事权利,商标注册是一种公开的权利取得方式,具有较高的公信力。所以对于注册商标,首先要推定其权利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注册商标权的效力是不容置疑的,所有推定的权利效力都可以被推翻。如果有明显证据证明商标注册是恶意的,可以推翻商标权的公信力。日本学者认为,如果一个商标被恶意注册,“没有实质性的理由认为只有在该商标被注册的情况下才应该给予法律保护,因为这种权利的行使显然是权利的滥用”[4]。而且商标注册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商标的符号构成是否合法,大量的违法原因在审查阶段是无法检验的。因此,商标注册的公信力是有限的,主要证明力仅限于“商标的符号构成合法”,至于商标注册是否侵犯在先权利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审查阶段难以查明,因此注册本身无法得到保障。总之,商标注册并不是合法性的绝对证明。然而,我国司法和执法机关往往将注册商标权误解为“行政机关授予的权利”,认为其效力不容置疑,都应受到“保护”。根据一项调查,一家公司专门注册与他人使用的未注册商标相似的商标。该公司声称:“一旦我们拿到商标注册证,我们将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向工商部门举报。对方侵权基本上是警告的问题。”[5]权利救济部门对登记效力的迷信,再加上宽松的登记条件,无疑会吸引更多的人以登记的方式在圈地上签名,甚至会助长更多隐藏的恶意登记行为。登记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加强权利的稳定性,减少权利冲突。然而,由于权利救济机构的误读,登记成为恶意圈地人的“洗钱程序”。
遗憾的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处理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两个注册商标客观上可能造成混淆,注册人是善意注册的,双方都没有过错,法院不应认定侵权,注册机关出于保护消费者的目的撤销一方注册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一个注册人有明显的恶意,其注册行为本身就构成侵权,那么法院为什么不给予救济?本函确立的原则,拖延了合法权利人获得救济的程序,使“登记”成为部分恶意当事人的保护伞,无疑会吸引更多的登记圈地行为。
(二)过度漠视商标使用的效力
赋予一个符号以商标本质的是实用。在不断的商业使用中,消费者逐渐将一个符号与特定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联系起来,使该符号真正成长为一个商标。然而,在救济程序中,司法机关往往过度使用和重新登记。
在“山西房山县老传统公司诉山西兴化村汾酒公司”一案中,①原告在白酒上注册了“佳佳”商标,但从未实际使用过。在注册之前,被告已经生产了北方品牌“佳佳九”,原被告已经协商了合资合作。原告申请注册的商标在符号构成上与被告实际使用的商标基本相同,原告主张被告销售“佳佳九”的行为侵犯了其商标权。从原被告的交往历史和原告的注册商标与被告使用的商标的一致性来看,不难看出原告的注册明显是恶意的。原告只进行象征性圈地,被告诚实使用商标。正是被告的生产和销售使“家家户户”真正成为一个商标。如何权衡两者的利益,结合商标法保护市场声誉的立法目的,不难做出取舍。但一审判决赫然写道:“商标的使用不一定产生商标专用权,商标只有在注册后才能受到保护。”可以想象这句话会如何诱导象征性的圈地。
(三)符号价值的误判
《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金额,是侵权人在侵权期间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侵权期间遭受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在司法实践中,商标所有人往往很难直接证明自己的损失,因此按照侵权人的利益计算赔偿是一种常见的方法。但该条款预设的“商标”是实体意义上的商标,体现的是市场信誉。只有这样才能推定侵权人借用了商标所有人的名誉,侵权人的收益被权利人损失。如果注册人的商标从未被实际使用过,而只是空的符号,则不能推定侵权人的收益为权利人所失。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不区分符号价值和商标价值,以侵权人的利益为赔偿依据。既然符号可以得到与商标同样的保护,那么人们热衷于通过注册的方式将符号封闭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显然,这种救济原则“会鼓励人们注册和囤积大量商标,等待他人侵犯自己的商标权并收取利润,这显然与商标法保护商标权的主旨大相径庭”[6]。
(4)“商标使用”与“符号使用”的混淆
对于“权利行使中的符号圈地”,现有的权利救济制度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因是一些执法、司法机关不承认什么是“商标使用”,将合法的符号使用视为侵权,使得符号垄断得到制度的支持。宝洁公司诉上海晨轩智能科技发展公司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②。原告在洗涤产品上注册了“保障”商标。被告是一家生产安全产品的企业,注册了“保障”域名。com。cn”。法院认定,被告的注册是使用原告的驰名商标,构成不正当竞争。由此可见,法院首先认定符号“保障”为商标。“保障”是一个有意义的英文单词,意思是“安全注意事项”。除了特定的商品之外,“保障”只是一个词。生产安全产品的企业选择“保障”作为自己的域名,是一种非常自然合理的商业选择,在竞争中没有什么“不公平”。判决书指出:“在被告晨熙公司申请将‘保障’注册为其三级域名之前,其在‘保障’本身并不享有任何合法权益。相反,被告应当知道,原告的‘保障’注册商标在市场上享有良好的声誉和广泛的知名度。”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符号和商标的混淆。对于“保障”的象征意义,没有人享有“合法权益”。享有“良好声誉和广泛知名度”,是“保障措施”的商标含义,而被告使用的是“保障措施”的象征意义,所以原告的商标驰名与被告的象征使用无关。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支持了原告象征性的圈地行为,将原告的权利客体从商标改为“保障”二字。
可以看出,在我国现有的商标权救济制度下,注册商标优于真实商标,符号价值等于商标价值,商标权等于符号垄断,这是鼓励符号圈地的制度土壤。
第四,商标权救济制度的完善:遏制象征性圈地
(一)正确解释登记的效力
商标注册不能视为权利有效性的绝对证明,而是权利有效性的初步证明。商标注册的可信度要根据商标审查的内容来判断。对于复审中的商标标志构成的合法性、与注册在先商标的区别和相似性等关键检验项目,可以认定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对于商标审查中难以查证的事项,不能推定注册的公信力,如注册是否侵犯商标权以外的在先权利,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等。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注册是恶意的,司法机关可以直接认定注册本身构成不正当竞争,不能使商标注册成为恶意竞争者规避法律的工具。一切违反诚实经营习惯的行为都构成不正当竞争,司法机关要有系统的思维习惯,把整个立法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商标法》未明确列举的恶意注册行为,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原则或《民法通则》予以制止。有的司法机关太死板,只会援引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来认定恶意抢注。如果域名抢注商标不符合本条规定的“已经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力”,那就无可奈何了。所谓“众所周知”,目的是为了证明抢注者的“知情”。通过具体接触知道别人的商标不也是“知道”吗?司法的僵化只是恶意投机者的福音。
(二)注重实际使用的效益
在救济程序中,应注意保护商标的实质和实际使用中产生的利益。未使用的注册商标与实际使用的商标发生冲突的,应当首先判断注册是否是善意的,防止恶意圈地人通过注册制度侵占他人利益。如果注册人和用户双方都是善意的,就要考虑使用的程度是否足以让消费者识别来源,尤其是实际使用的时间。我们不能因为符号相似就贸然命令善意用户停止使用。如果注册人和用户都是善意的,但客观上可能在消费者中造成混淆,可以考虑要求用户附加适当的区分标记。
总之,如果当事人已经通过善意使用确立了市场声誉,裁判应当特别注意维护声誉利益,采取最不震撼的方式解决利益冲突,而不是简单地根据是否登记来确定保护方案。即使争议的符号在符号构成上相似,只要是通过使用获得的差异,就应该允许两者并存,不应该因为“标准”而丢弃“原本”。
(3)合理的损害估计
由于我国并不要求商标注册时实际使用,虽然商标实际上是一种符号,但只要是善意注册的,仍然受法律保护。他人未经许可使用该商标的,构成侵权。但在确定损害赔偿时,不能盲目以侵权人的利润作为计算依据。未实际使用的商标没有真正的市场利益,他人获得的市场利益不能推定为商标所有人的损失。但非法使用他人商标节省了独立设计成本或许可费,构成不当得利。因此,更合理的救济方式是:“商标所有人有权要求侵权人按照不当得利返还合理的商标许可费。”[6]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商标许可费”应该与商标设计费相比较,而不是与已经建立了真实市场信誉的商标许可费相比较,用户获得的利润不应视为“不当得利”。这种许可费本质上是“符号许可费”,类似于智力成果的价值,即符号形式本身的价值,而不是真正的商标价值。
(4)区分“商标使用”和“符号使用”
“权利行使中的象征性圈地”有相当一部分不是故意的,实际上是由于认知障碍。但是对于专业的权利救济机构来说,混淆“商标使用”和“符号使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救济机构能够做出正确的判决,判决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教育工具,让商标所有人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范围。区分“商标使用”和“符号使用”,必须深刻理解商标的概念,记住商标之后必须有“商业导向”——市场信誉。如果使用的符号在消费者眼中与商品或服务的原产地无关,那么使用的对象就是简单的符号而不是商标。
动词 (verb的缩写)结论
象征性圈地的奇怪现状虽然反映了人性不诚实的一面,但也有纵容人性劣根性的制度根源。商标权救济制度的重构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商标的价值来源于使用,投机性的圈地所有者一定不能伤害诚实的使用者,未使用商标的救济是有限的,商标权绝不是象征性的垄断。
上一篇:非典型侵犯商标权行为的认定
下一篇:商标权客体